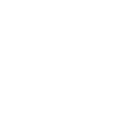地窑子
从凤凰池生态谷景区一路往山上走,骊山的五条山麓像龙爪的五指一般深深插入大地,上山的路都是沿着两“指”形成的沟谷在山脊上修建。行至半山腰,整个幽深茂密的山谷就会完全展现在面前,秋日是满山斑驳的色彩,远处还能依稀看到下游水库一潭静水反射的莹莹波光。绝佳秋景的理想观赏地是老郭家的场院。2011年才新建起的二层小楼正对着山谷,向南距离山谷边沿不过100米左右,视野极其开阔。天气暖和时候,老郭家的餐桌就摆在院子里,沟谷的荒坡曾是老郭的石榴园。2010年,杨寨村被列入临潼度假区的征地范围,直至2012年4月,全村7个组的土地全部被征。土地主要被纳入骊山景区浅山生态涵养带绿地林网,成为度假区绿色旅游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
杨寨村村民老郭夫妇和刚从肯尼亚探亲回来的二儿子郭小峰
老郭本名叫郭忠民,是杨寨村夏二组的副组长。属虎的老郭虚岁已经65,但壮硕的身材、黝黑的肤色让他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叫一声“老郭”是外来者对好客的主人表达的亲近感,无论是否认识,走进院子,老郭就会拿出自家种的石榴、晒的柿饼来招待,更不会少的是一杯香甜的蜂蜜水,蜜蜂也是他自己养的,蜜源就是沟谷中的石榴和各色野花。
老郭家有5亩责任田,1984年时他还承包了24亩地大小的一片荒坡,而当时整片荒坡30年承包权的总价只有80块钱。2012年的征地补偿中,老郭的5亩石榴园依据的补偿标准是4.5万元/亩,荒坡整体作价11万元。如今不用再料理果园的老郭闲不住,他的房前屋后栽满了各种花草和果树。“从草莓、樱桃、杏、桃、葡萄、石榴到柿子,我这里四季水果都不缺。”除了到手的30多万元征地补偿款,老郭眼下没有其他营生。以他的园艺手艺,有朋友劝他到度假区的园林绿化公司去找份工作,他不肯:“我要是想挣钱也不会等到现在。”
老郭家的新房子没有上楼的楼梯,一架架在墙沿的木梯子成了上下楼的工具,这让整栋小楼显得有点滑稽。大儿子和女儿都已成家,家里只有老郭夫妇和二儿子郭小峰住,一层的三间房就已够用,目前二层除了用来晒黄澄澄的柿饼,全都闲置着。这种没有楼梯的奇怪住宅在杨寨村比比皆是。原来,虽然度假区的拆迁政策已经落实为每户按照人口、每人65平方米的标准补偿,村里人总还是希望能够加盖一些,以防拆迁政策变化时自己不会吃亏。
杨寨村住宅的拆迁时间表还没有人知道。老郭听说也许一年后,郭小峰听到的消息则是最快3~5年。事实上,杨寨村究竟是整体搬迁还是原址保护,度假区也没有做出最后的决断。2010年,在度假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上山逐村探访、了解情况时,谁也没想杨寨村还保留着极具特色的民居建筑形式——土窑子。这使得杨寨村在发展农家乐旅游上具备了更好的优势条件。
循着小路走进新房子东侧一片隆起的土坡上的石榴树林,走到坡顶向下望才会明白什么叫“别有洞天”:脚下的是一个隐匿在垂直距离8米深地下的长方形场院,长15米,宽5米,内侧共开凿了7口窑洞。在2011年搬进新房前,老郭夫妇几十年都住在这个地窑院子里。
盘旋下降的小道是老郭自己整理出来的,一直可以通到土坡底部的大门。地窑子的排水考虑很周全,门两侧挖有储水的水槽。“夏天顺着坡道流下来的雨水可以往两边分流,就不会流进院子里了。”方正的院子中间是已经荒弃的菜地,四壁的窑洞每间都有十几平方米,窑洞里砌着土炕,冬日里烧柴火既可取暖又可祛湿。
最初“发现”老郭家地窑子的是当地摄影师李大卫。李大卫和老郭相识在2009年左右,沿骊山拍摄风景的他与在石榴园里劳作的老郭攀谈,热情的老郭邀请他到家里去坐坐。“当时我正在院子里摆了个小矮桌上网,李老师从窑顶上往下一看,这么传统的建筑里竟然坐着人在用笔记本电脑。”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完美场景让李大卫欣喜不已,他告诉本刊,窑洞多分布在陕北地区,关中地区比较少见,更何况是在地下挖掘的“地窑子”。李大卫后来了解到,杨寨村还留着三十几个荒弃的地窑子,“据我所知,老郭是临潼最后搬出来的一家”。
村里的大多数地窑子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产物。老郭说:“修地窑子是无奈之举,挖窑洞用不着建筑材料,只要有力气,那时候人力也不值钱。”父母年老,老郭唯一的姐姐已经嫁人,身为独子的他是家里挣工分和挖地窑的唯一劳动力。直到1970年,原籍陕南柞水的耿素琴嫁入郭家,老郭才有了劳动和生活上的帮手。住了十几年的地窑子,耿素琴落下了严重的肩周炎。
2010年,临潼地区连续大雨,老郭夫妇被斜口街道办事处强令搬出地窑子,以防发生意外。它们新的房子也是在这样的契机下才得以盖起来。
土地价值的再认识
杨寨村是临潼典型的浅山区村庄,因为土地不平整、用水困难,土地产出价值低一直是限制村民经济水平提高的重要问题。2011年,临潼度假区对所辖范围内各村所做的社会经济状况调研报告显示,杨寨村有38%的人人均年收入在6000~7000元,还有22%的人在4000元到6000元,超过半数人口的人均年收入在临潼区人均年收入的7600元以下,高出人数比例不过全村443户1504人的20%。
老郭家居住了十几年的地窑
1968年,从斜口中学初中毕业后的老郭回到村里生产队参加劳动,杨寨村的主要种植作物是小麦、苞谷和棉花,当时小麦的亩产只有240斤左右。“每年二三月开春,家里的口粮就特别紧张。”耿素琴说,没有办法,只能用40斤小麦去和人家换80斤苞谷,“苞谷粒晒干了,碾成粉,4月就靠苞米糊糊才能熬过去”。严重缺粮的情形在1982年土地分产承包到户后有所改观。回想起来,老郭觉得该归因于“那几年雨水好”、“粮种也比从前的好”。亩产到400斤左右的产量总归够全家不会饿肚子,但当时平原村庄的亩产在分产到户后都已经达到了六七百斤左右。
制约杨寨村农业发展最主要的问题是缺水,郭小峰的童年噩梦除了挖窑,另一项就是打水。“一口井有54米深,上面是一圈窄井口,井底下已经塌得可以停辆卡车。”旱季时这样的深井出水也很少,桶放下去一次也只能打到少半桶。这样的水源也只是能维持日常家用,农田里的庄稼还要是靠天吃饭。自然条件的落后制约着杨寨村土地耕作效率的提高。
1984年杨寨村里搞荒坡承包时,根本没有人和老郭竞争。老郭把20多亩的荒坡全部种上了石榴树苗。种石榴是无奈下的因地制宜,“石榴比粮食耐旱,一个石榴就有半斤多、产量高,我们这里更适合种石榴”。石榴树5年挂果,到征地前,老郭家的石榴亩产量可以达到2000多公斤。“光景最好的一年,石榴的地头收购价格就有8块钱一斤。”老郭回忆。即便如此,一年六七万元的收入也是土地给予老郭夫妇的极限。杨寨村超过25%的人外出打工,像老郭夫妇这样靠老人料理土地的情况比比皆是。
相比靠近城区的村庄,除了土地产出的差距,杨寨村的村庄基础建设都要相差5年的发展水平。郭小峰靠摩托车代步,这是在泥泞不平的山路上最有用的交通工具。山上的手机信号也不稳定,沟通和交通是杨寨村发展无形的障碍。
龚吕村和杨寨村毗邻,龚吕村坐落在芷阳湖与凤凰池生态谷之间、生活条件比杨寨村更为不利,当地属滑坡地带,不易打井,缺乏水源,人畜饮水都没有保障。但是龚吕村居然引来了新加坡悦榕集团的酒店开发合作项目。老郭不知道意大利的托斯卡纳,他更不明白悦榕集团选中的这个山谷和托斯卡纳有何相似之处,他更难以理解的是龚吕村距离骊山国家森林公园仅2公里,保持了千年农耕生活的山塬地形在世界一流酒店开发者的眼里兼具了生态价值和观赏价值。
老郭对家乡自然风光的美有着朴素的认识,他享受着清早被几十只鸟儿的合唱叫醒,然后在树林里散步、看神采奕奕的野鸡穿梭。这也让他朴素地认同度假区绿色生态旅游的发展理念:“咱还要让更多的外地人来咱临潼看看,看看咱这日子美不美,再尝尝咱这不掺假的地道蜂蜜,叫他们知道咱这儿就是宝地。”
老郭还没深刻意识到,他的地窑子并不比龚吕村的“托斯卡纳”逊色。建筑本身浓郁的地方特色,再加上老郭家庭生活史声情并茂的演绎,对于游客来说,地窑子和杨寨村的环境一起就构成了生态价值和人文价值相结合的体验型目的地。所以,在李大卫“发现”老郭的地窑子后,2010年度假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也成了这里的常客。几十个地窑子让人惊艳,但如何能被有效利用起来也成了规划中需要考虑的问题。
两代人的选择
与高沟村村民情况相反,耕地被征收的杨寨村村民已经实现了户口的“农转非”,这些依然居住在半山腰上村落里的人成了彻底的城镇居民,区别只是就地转化,还是整体搬迁。正因为信息的不确定性,老郭一家人从各自的生活出发也各有想法,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能代表杨寨村村民的一般情况。
郭小峰38岁,眉眼间极像老郭,尤其是剃得锃亮的光头,只是肤色白皙,不用在田间劳作,他也就不再有阳光留给父亲那般浓重的古铜色泽。郭小峰在海外的石油钻探企业中给中国工人当厨师,一年里只有两三个月的假期可以回国探亲。2007年,他第一次前往吉尔吉斯斯坦,之后多年都在肯尼亚工作。
每次从肯尼亚回国,郭小峰总要花上一两万元给家人买威士忌、葡萄酒和巧克力等各种礼物,老郭喜欢南非的葡萄酒,一个人喝光了全部。但在家里,他却基本不和儿子谈论肯尼亚的生活见闻。“他没兴趣听,其实他到现在都反对我出国。”郭小峰说。老郭对外面的世界没什么兴趣,安于生活现状才是让他满意的:“咱能看着临潼越来越好,越来越美,心里也高兴,以后也不用去他外地啥地方旅游去,咱这地方啥没有?”
厨师是1996年郭小峰高中毕业时自己选的职业。“全班只有两个人没有考上大学,其中一个是我。”郭小峰陷入过迷茫,但是摆在他面前的职业方向可选择的余地并不大。“谁不想去事业单位找个安稳工作呢?我这样农村户口的孩子又没有学历,门槛实在太高了。”老郭从没干涉过三个孩子的选择,书读不下去了就去谋生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他也是这么过来的。郭小峰倒是想得很清楚:学一门技术可以吃一辈子。最后他在裁缝、理发师等几个职业里选择了去读烹饪学校。
从烹饪学校一毕业,郭小峰在当地一家学校附近开家泡馍馆,不到一年,就因经营不善赔光了本钱,他一气之下跑去了新疆。在新疆闯荡的郭小峰4年才回家一次,当厨师总归发不了财,这也不是他谋生的第一选择。“我卖过袜子、卖过安利,只要能挣钱,不违法的事我都肯去做。”回想起早年在社会闯荡的经历,郭小峰感慨,“就是小时候穷怕了。”他记忆里始终抹不掉的是哥哥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初中没毕业就到砖厂去打工挣钱。
折腾了一圈,郭小峰还是回到了厨师的岗位上。几年的海外生活经历让他的视野发生着变化,他不仅融入了城市生活,也开始拥有国际视野:“别看肯尼亚是非洲国家,人家开车都特别规矩,你要过马路,向司机示意,人家都会停下来等你通过。”“我这几年从北京回临潼,一次火车都没坐过,全是坐飞机。”郭小峰说起来很是得意。
郭小峰的大哥现在临潼做室内装饰,一年有着七八万元的收入。房子虽然还在村里,但为了方便工作,一家人早就搬到了临潼城区,一个月的租金也要1000多元。刚满20岁的大侄子是郭小峰难以理解的“90后”,初中毕业后就辍学打工去了。“他在彩印店学彩印,一个月有三四千元的收入,却一分钱也剩不下来。”现在村里年轻人结婚的成本已经达到十三四万元,汽车成了标配。“不能住在村里,买不起也要在临潼区里租房子。”去年夏天,郭小峰介绍侄子去广州打工,月薪可以拿到5000元,结果不到一个月人就跑了回来。“他说广州太热了,挣了1000块钱,却坐飞机回来花了1300元。”
老郭唯一的女儿在做全职主妇,四口人的家庭唯一的收入来自扎灯笼卖的丈夫。灯笼的市场需求小,他还要四处打零工来补贴家用。但是夫妻俩把孩子的教育问题看得很重,在郭小峰看来走向了一个极端。“周末还都给报满了补习班,让娃做完作业玩一会儿都不行。”妹妹在斜口镇上花四五百元租着一间房,管教、照顾两个孩子就是她的工作。郭小峰说:“娃也懂事,大的跟小的说要好好学习,不然就得跟姥爷以前那样受穷。”
拆迁的利益对于郭小峰兄妹三人显而易见:大哥一家再不用租房度日,侄子的婚房或许也能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妹妹无论是把孩子们转到城区的学校就读,还是在新社区建设的新学校中就读,无疑都将享受更好的教育质量。再过一个月,郭小峰就要启程回肯尼亚,但是他说这可能是自己的最后一次远行。度假区的发展让他看到了机会,未来潜在的客源量让他希望能够在临潼创业搞餐饮,他觉得一年后归来应该能看到更明朗的契机。
老郭夫妇对故土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他真心热爱园艺,精心经营着自己的院子里的“植物园”,山坡上一株尚未凋谢的“金线蝴蝶”可以让他乐到眼睛放光。他也舍不得他的地窑子,那里有他几十年的回忆。这两三年,随着包括度假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在内的诸多朋友到访,老郭也认识到了土窑子的旅游经济价值。他动过自己搞农家乐的念头,“但是没有人啊”。相比客源,他愁的更多是没有帮手来做成这件事。除了人手,已经荒废的土窑洞如果想转变成可以接待游客的宾馆,安全加固、房间改造以及上下水等现代化改造的投入也不是老郭拿征地补偿款就可以承担的。而且,地窑子也只有在具有一定规模后,才值得成为游客旅游线路中的一个目的地。毕竟这里不是临潼的黄金旅游线,距离兵马俑景区还有11公里。
老郭无法完成的事情恰恰是度假区有能力去做的。目前,建设高端养生的“窑洞农家乐”,已经被纳入紫霞生态谷建设的规划中。在度假区的发展规划中,保留原有特色村镇“以旅促农、以旅哺农”也是绿色城乡统筹的重要发展路径之一。搬迁还是留守?这不仅是老郭要从情感上盘算的事,也是度假区从长远利益上要盘算的事:生活在原有土地的农民如果能就地实现生活方式和经济方式的转型,未尝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整体搬迁,还是原地保护:老郭的权衡
2013年12月26日 10:49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贾子建
文章来自:中国城乡规划行业信息网

 END
END

专题PPT,交流社群

数据教程,交流社群

仅限规划管理工作人员加入
| 小编工具:无版权免费可商用图片搜索 | 规划行业搜索聚合 |
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 13132097@qq.com:规划头条 » 整体搬迁,还是原地保护:老郭的权衡
 规划头条
规划头条 何镜堂:如何做好新型城镇化的中国建筑
何镜堂:如何做好新型城镇化的中国建筑 地方打响扩容战 中国城市群前景展望
地方打响扩容战 中国城市群前景展望 2014年实施的与城镇化相关的规范
2014年实施的与城镇化相关的规范 Facebook正在使用你的资料来跟踪全球城市人口迁徙趋势
Facebook正在使用你的资料来跟踪全球城市人口迁徙趋势